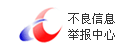在中华文明的浩瀚长河中,山东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山东不仅是齐鲁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儒家思想的摇篮。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山东博物馆如同一座巍峨的文化灯塔,守护着数千年的历史记忆,向世人展示着齐鲁大地的辉煌与灿烂。
山东博物馆(原山东省博物馆)成立于1954年,坐落于山东省济南市,藏品以富有地方区域特色的历史、自然、艺术类藏品为主,其中陶瓷器、青铜器、甲骨文、简牍、汉画像石、服饰等收藏尤为丰富,涵盖了从史前时期到近现代的各个历史阶段,堪称一部立体的“山东通史”。
两院合并——山东博物馆初立
山东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04年成立的济南广智院和1909年成立的山东金石保存所。
1887年,英国传教士怀恩光在青州创建博古堂,1904年,博古堂迁至济南扩建并更名为广智院,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博物馆之一。
广智院开馆当天便门庭若市,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巨头鲸、扬子鳄、大熊猫、金丝猴等各种动物标本,冰川、河流、高山等地壳变动的截面模型,银河、太阳、月亮、地球的仿真运转……大量过去人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展品,把一个精彩纷呈的外部世界展示于众。黄炎培、老舍、胡适等对广智院都有很高的评价,此后“到广智院看西洋景”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选择。
稍晚于广智院,1909年1月25日,山东巡抚袁树勋上《奏东省创设图书馆并附设金石保存所以开民智而保国粹折》,随后获准。山东金石保存所是国内首家省级地方政府创办的博物馆性质的机构。1929年,著名考古学家王献唐任馆长后,着意搜集文物,扩充馆藏,至抗战前,藏品达到17000余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使珍贵文物免遭涂炭,王献唐与编藏部主任屈万里、工友李义贵,携5箱馆藏珍品辗转万里,将其运至四川乐山保存。护宝期间,王献唐说:“这是山东文献的精华,若有不测,我何以面对齐鲁父老,只有同归于尽了。”李义贵出发的时候,刚出生的儿子还不到1岁,而这一守就是13年,直到1950年,这批珍贵文物始返故乡。
新中国成立后,地方博物馆的筹建逐渐纳入议事日程,山东省博物馆幸运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座省级综合性地志博物馆。当时的馆址分为东西两院,东院位于济南市广智院旧址,西院位于济南道院旧址。1954年,山东省博物馆成立后,将广智院旧址辟为自然陈列室、济南道院旧址辟为历史陈列室,而山东金石保存所南迁文物中的珍品和广智院的部分展品则为山东省博物馆打下坚实的藏品基础。
1992年10月,山东省博物馆位于千佛山北麓的新馆落成开放。进入新世纪,为了适应时代需求,山东省博物馆新馆建设又一次提上日程,新馆选址在济南市区主干道经十路东段,2010年11月16日正式向社会开放,并更名山东博物馆。
山东博物馆的建筑外形取自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世界的认知,上部为半圆形穹顶,下部为四角内切立方体。圆,是中国道家通变、趋时的学问,方,是中国儒家人格修养的思想境界。圆方互容,儒道互补,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同时也将齐鲁文化刚柔并济的思想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山东作为华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以“天圆地方”为设计灵感,无疑是最为庄重贴切的隐喻。这份设计巧思,赋予了整座建筑一种与生俱来的庄严雄浑气质,哪怕还未踏入馆内,仅仅是远远观望,敬畏之心便已在心底悄然滋生。边长136米的正方体外观稳重大气,下部立方体结构在四个角度进行了模式化切削,使四个角部呈现出棱柱状结构,让建筑显得灵动而且富于朝气,避免了方正建筑的古板生硬。正方形上方中央的穹顶采用半圆形白色材料分隔,在兼顾室内采光的同时,如同一簇簇向上涌起的浪花,象征着泉城济南的“ 天下第一泉”趵突泉,立面采用灰色花岗岩,象征着巍巍泰山。
踏入博物馆内部,挑高的中庭空间更是震撼人心,室内设计依然延续了“天圆地方”的思想,同时,在装饰方面更具地域特色,黄色的地面象征着母亲河黄河,高耸的台阶象征着五岳之首泰山。在顶部中央,悬浮的墨绿色玉璧如截取了一段春秋夜色——这方300平方米大玉璧的设计灵感取自鲁国故城曲阜出土的战国玉璧。玉璧中孔与建筑外部穹顶透光部位相对,由此,自然光倾泻而下,呈现出别样的光影效果,极具艺术美感。当人们从地下层的史前文明展区逐步上升至顶层的近现代展厅,如同行走在历史长河之中,形成“登临泰山”般的游览体验。
无双黑陶——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
提起山东,今天人们第一印象就是“孔孟之乡,礼仪之邦”,但在孔孟之前的悠远漫长时间里,山东的远古先民东夷留给人们的却是一个模糊的背影,先秦时期,这个族群曾和西戎、北狄、南蛮并列,曾被视作是落后野蛮的边缘文明。但当历史尘埃落定之后,人们发现,正是东夷先民抟土成器散发的质朴光泽,闪亮着九州最初文明的晨曦。
“拱着鼻子、张着大嘴、腹部浑圆、翘着尾巴”,眼前这个萌态十足的陶器,便是馆藏于山东博物馆的“网红小猪”——红陶兽形壶。它的脑袋和身体像猪,耳朵、四肢和上翘的尾巴又像狗,因此它有了一个很中性的名字“兽形壶”。
1959年,红陶兽形壶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距今4500-6200年),虽然历经数千载春秋,但当我们透过玻璃展柜与它相望时,依然能感受到那原始的生命律动——大约5000年前的某个黄昏,汶河畔一位陶工蹲在陶窑前,望着泥窝里打滚的小猪,小狗翘着尾巴来回奔跑,晚霞将天际晕染成一片橙红。他用手中湿润的陶土留住了这天真美好的一瞬,于是壶嘴有了翘起的鼻头,壶底化作支棱的手脚,色泽明丽,活灵活现。人们说器物有灵,或许说的就是这样的瞬间,原始先民把对生命的观察揉进陶土,从实用性中涵养出鲜活的灵魂。
今天人们在喜爱它生动可爱造型的同时,更感叹它极具实用的巧妙构思,陶壶的所有用途都融入造型之中,使用时只需从壶尾部注水,在腹下进行加热,再提起背部的把手,就可以将水从小猪嘴里倒出。其形态下,蕴藏着先民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礼赞,也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精神世界的立体投影。
仰首的红陶兽形壶并非孤独的传奇,隔着千年时光,蛋壳黑陶杯的玄色锋芒正刺破新石器时代的黄昏。
凝视它,黑暗突然有了重量,在多姿各异的彩陶世界中,它如此与众不同:空灵精美,体态修长,通体乌黑。这种神秘的黑色金属光泽,带着直观的视觉冲击和震撼,让人无限敬畏,眼前的这件陶器名叫——蛋壳黑陶高柄杯。
1929年,在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发现了距今4000年以上的历史文化遗址,考古学家将其命名为龙山文化(距今4000-4500年)。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就是“黑陶”,它跟彩陶完全不同,乌黑发亮,给人一种至纯至坚之美。其中尤以蛋壳黑陶最为精美,其陶胎之薄,无与伦比,一般厚度在0.2-0.3毫米,最厚的地方也不足0.5毫米,以“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掂之飘忽若无,敲击铮铮有声”而闻名于世,被世界各国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
山东博物馆的蛋壳黑陶高柄杯便是其中的翘楚,代表着“黑陶文化”的最高水平,它以0.2毫米的薄胎挑战着人类手工艺的极限,将新石器时代的文明推向了难以复制的艺术巅峰。今天人们在陶胎上还能看到明显的转轮痕迹,而这正是蛋壳陶薄如蝉翼的秘密——使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快轮拉坯法”。如此薄壁的陶胎在快速旋转中非常容易破碎,今天人们用电子显微镜分析它的成分,用3D打印复刻,却始终造不出那份流传千年的幽光。
蛋壳黑陶并非批量生产,耗费如此的人力物力去达到一种极致,也许只有作为礼器才能合理解释它的存在,用规范化的系统与工艺极致的器物来表现祭祀中虚幻的礼仪,这是权力与等级的诉求,也预示着人类社会新的秩序慢慢形成。作为山东地区史前文化鼎盛期的巅峰之作,蛋壳黑陶是东夷文化最耀眼、最富有标志性的文化符号,而以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标志性的文化发展阶段,它上承大汶口文化,下启青铜时代。
商周代序——青铜激荡的金石之声
当陶器的质朴光芒逐渐淡去,历史开始迈入了青铜时代,青铜器不仅是技术革命的标志,也是先民从共情自然到征伐扩张的精神转轨。
展厅中的“亚醜钺”便见证了这历史一幕,这尊青绿沁骨的钺器透雕人面纹,五官微突出,双目圆睁,嘴角上扬,口中露出城墙垛口似的牙齿,口部两侧对称地铭有“亚醜”二字。商代崇尚鬼神和占卜,因此青铜礼器大多塑造出神秘可怖的形象,这是商王借助神权来巩固自己统治的手段,让人产生一种神圣的威严狞厉之美。
今天人们看到这个瞪着铜铃大眼的青铜表情包,或许觉得呆萌,但它背后却藏着商王朝最血腥的秘密。1966年,考古学家在青州苏埠屯1号墓发现它时,还发现了48具人殉,这甚至超过了河南安阳的殷墟妇好墓。专家推测,这应该是商王朝控制下的方国墓地,因为钺在古文献中记载是“大斧也”,属于一种斧类兵器,到了商周时期,钺代表的是王权和军事统帅权,说明能够拥有它的人地位很高,且拥有着强大的兵权,墓主人可能是仅次于商王的方伯一类的人物。
既然亚醜钺如此重要,那为何会出现在山东境内呢?
这要从商王朝和山东渊源说起,传说商族起源于山东环渤海一带,由东夷族玄鸟氏一支发展而来。商始祖契大约与禹同时,因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被舜任命为司徒,封于商。契的活动足迹就在今天的鲁西豫东地区。为对抗夏王朝、保卫自身,商族与东夷族结成政治军事联盟。公元前16世纪,商朝建立。商王朝采取据点式的推进方式,逐步加强对周边地区的控制。
历史上著名的盘庚迁殷,说的就是商朝第二十代王盘庚,为了避免自然和政治危机,将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自此,商朝进入强盛期,《诗经•商颂》记载:“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而东方地区因为拥有丰富的海盐和金属等资源,更是成为晚商王朝重点拓展和经营的区域,随着商人在东方的统治势力持续东移,相继控制东部的淄河、游河流域,最终发展到潍河一线,青州苏埠屯遗址成为东方边境线上的重要据点,亚醜钺在此出现也就不足为奇。
商人对山东地区的经略,加强了商文化与东夷文化的交流融合,这也为山东地区融入中原文化圈奠定了基础,但文化融合的背后往往伴随着征伐。商夷之争贯穿整个商代,商代晚期愈演愈烈,这也是加速商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据《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与东夷的作战耗费了大量国力,而彼时西边的周人势力却在不断发展壮大,最终间接导致牧野之战中“前徒倒戈”的溃败。
随着周王朝的建立,商人在山东地区经略多年的势力逐渐被周人取代,周天子将核心家族分封于齐、鲁。齐鲁两国在不同区域以不同形式与东夷文化交流融合,岁月流转,这片土地迎来一个后世广为流传的名称——齐鲁大地。
摘自 中国建设报公众号 2025.03.25 常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