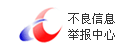“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当大唐浪漫诗仙李白挥洒乐府《蜀道难》1200多年之后,在古蜀国故地成都平原一个叫“三星堆”的地方,忽然有了惊天发现:一大批骇世惊俗的青铜、金银、玉石、象牙等文物喷薄而出,让此前缥缈流传于神话、只言片语于史籍之中的古蜀国,渐渐撩开了神秘的面纱。
“三星伴月堆”——在传说与史实之间
三星堆,原本就是四川省成都市偏北的平原上三个起伏相连的土堆,具体位置是现在广汉市南兴镇三星村。三堆土北隔马牧河与月亮湾台地相望,清代以来雅称“三星伴月堆”。直到1929年,当地农民燕道诚一锄头下去,刨到了直径半米的大石璧,接着发现了400多件玉石器物,从而,一个被称为“20世纪人类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的古蜀国文明遗址揭开了帷幕。这时,人们才发现,那三个土堆其实并非风雨的雕塑,而是夏商时期古人夯筑城墙的劫余。残垣由于数千年的自然力量和人类活动,渐渐剥落成一条起伏错落的土埂。从此,“三星堆文化”也以神秘、凌厉的姿态迅速切入大众的视野。
从1929年开始陆续挖掘,三星堆文物不断涌现。尤其是1986年一号、二号器物坑(祭祀坑)出土了6600多件品类丰繁、璀璨精奇的文物,震惊了世界。三星堆文物深寓独特的文化信仰与价值观念,具有深邃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艺术特色,在世界上也属于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最富观赏性的文物品类之一。在这些旷世神品中,有以神秘诡谲的青铜雕像、铜神坛为代表的青铜器群,有以流光溢彩的金杖、金面罩为代表的金器群,还有以“祭山图”玉璋、神树纹玉琮为代表的玉石器群等,令人目不暇接。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三星堆从各个侧面向人们展现出一个梦想充溢、气象万千的古蜀文明。考古学上的“三星堆文化”是指年代为公元前2100~公元前600年集中分布于成都平原及东部的峡江地区的一支考古文化,距今约4100年到2600年前,相当于黄河流域的夏、商和周初,其发展程度远远超出人们对于古代四川的认知。
一直以来,上古的四川地区都被看作是几无文化可言的戎狄之域,有信史的年代已经到了战国时代,即秦灭巴蜀的公元前316年(距今2300年前),史书记载巴蜀人民摆脱野蛮、爱好文雅也是从汉景帝派文翁入蜀教化才开始的。《说文解字》《水经注》《蜀王本纪》等文献中都有关于古蜀国神话的零星记载,这些书有的已经亡佚,只有佚文还保留在其他书的引文里面。根据这些零星的古史传说和文献记载,在秦帝国将四川盆地纳入其版图之前,盆地西部平原上曾有一个历经夏、商、周三代的古老国家——“蜀”,它创造过非常繁盛的文明,甚至殷墟甲骨文中也多次提到与“蜀”的往来。一直到李白生活在四川的唐朝,古蜀国历史仍存在于神话和传说中。传说蜀人的始祖“蚕丛”及其民众居住在川西高原上的岷山地区,被称为“蜀山氏”,其后另一位首领“柏灌”带领部分人东进成都平原,又经过“鱼凫”“杜宇”“开明”三个时代,最终于公元前316年被秦所灭。三星堆文化虽然没有文字自证,但它的位置、年代、文化特征和内涵,都与传说中的古蜀国极其吻合。所以,目前学术界一致认为,三星堆正是古蜀国的遗址,并且应是该国的中心都邑。
“堆列三星、古蜀之眼”——古蜀文化新家园
在三星堆遗址以北不远处,有一条鸭子河,注入长江的支流沱江。河畔有着成片的湿地森林,远眺可见连绵的雪山。在大地自然景观的背景映衬下,三个连续的现代堆体建筑神秘而恢弘,这就是以“堆列三星、古蜀之眼”为核心设计理念的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文物宝贝们的新家园。
其实,早在1997年10月,当地政府为了收藏、保护出土文物和展示、研究三星堆文化,就在遗址的东北角建成了三星堆博物馆,成为几千件精彩文物安稳的家园和华美的舞台。该馆曾获得“全国首届城市纪念性建筑奖”“建国60周年建筑设计大奖”等众多奖项,只是随着考古勘探和重点发掘的不断深入,只有两个展馆的老馆已无法容纳新文物的展示,博物馆新馆的建设计划提上日程。
2020年10月10日,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和游客中心(新馆)概念设计方案面向全球开启征集,当时有来自国内外的57家设计公司及设计团队报名。经过激烈角逐,由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刘艺任总设计师的原创设计作品——“堆列三星,古蜀之眼”在众多方案中脱颖而出,成功中选。2022年3月29日,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正式开工,由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施工。2023年7月28日,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在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当天正式开放,从项目立项、破土到竣工,只用了485天,再次惊艳了世界。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主体是三个连绵起伏的覆土堆体建筑,是对古蜀王国三个堆状遗址文脉的呼应。而堆体建筑的几何曲面源自老馆二号馆。作为遗址公园中轴线尽端的制高点,二号老馆是三星堆著名的历史地标,是前辈建筑大师郑国英先生的代表作品。二号老馆经典的螺旋曲线外墙,延展成为新馆外形和内部空间曲线。堆体建筑屋顶采用斜坡覆土,朝着北侧河岸方向缓缓下降、融入河堤,与大地浑然一体。三个堆体建筑的平面夹角呈现严谨的几何图形,生成独特的形体韵律,寓意“堆列三星”。
“古蜀之眼”是指堆形建筑外立面两个巨大的玻璃窗设计,这两个玻璃窗就像三星堆青铜面具中的眼睛一样,是视线交流的核心。人们在建筑的内部可以眺望到三星堆遗址园区,也能看到远处的古城遗址,可以进行一场无声的、穿越历史的对话。
三星堆博物馆中庭的“时空螺旋”是馆内参观动线的枢纽,360度环绕的坡道连接新馆地上地下主要的楼层。三星堆二号老馆标志性的圆形中庭朝向天空,象征“天眼”,代表着对天的崇拜,而新馆则创造了向着地心旋转的“地眼”,代表对大地的追寻,螺旋坡道盘旋而下,最终抵达建筑的最低点——地下负10米位置的圆形地坑。地坑的最深处,三束激光投影从圆孔中射出,在30米上方的天棚投出变幻的三星堆影像,寓意来自远古的文明之光。“天眼”与“地眼”是对天地关系的阐释,上天入地,连接起新馆和老馆,串联起古今,也串联起一个地域的文脉。
“王者之器”与“天山之祭”——古蜀王国猜想
古蜀国的历史虽然因缺乏记载而“茫然”,但是,三星堆横空出世的文物让世人得以一窥古蜀国先民独特的生存意象与瑰丽奇幻的精神世界,叹服这个上古族群非凡的艺术想象力与惊人的创造力,也让世人对古蜀王国的猜想有了实物依据。
在三星堆博物馆一楼“巍然王都”展览单元,展出一条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重约500克的金杖,金皮原本包卷在木棒外面,出土时木棒已碳化成渣。金杖一端有图案,上刻两个头戴五齿高冠、耳戴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还有鸟、鱼、箭的图案组合。学者推测,金杖可能与传说中的“鱼凫时代”有关,金杖集神权、王权于一体,是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王者之器”。
戴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是三星堆最引人注目的文物之一,57件青铜人头像只有4件戴了金面罩。戴面罩的人头像金光熠熠、尊严高贵、气度非凡。学者推测,如果说金杖象征王权及神权,代表统治权威,那么金面罩施于极少数铜人头像,则应是象征古蜀国的显贵。从这个意义上说,金面罩在古蜀文化中是神圣、尊贵、权威的代表。以金饰面,彰显神权与王权象征者容貌的神圣感、权威感。金箔薄如蝉翼,也表明当时捶打工艺高超,独特的纹饰制作和粘贴方法更是在上古时期独树一帜。其他如虎形、璋形、鱼形等金箔也都价值连城,在金器数量极为稀少的商周时期,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却出土了金器65件(不含残片、残屑),总重约850克,对研究我国早期黄金制品意义重大。
祭山玉璋出土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也是三星堆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之一。玉璋所刻图案构图风格奇诡精丽,其中有云遮雾罩、层峦叠嶂的高山,有或站立或跪坐、神情庄重的人物,有冉冉升起的太阳,还有从天而降、触于山腰上两只神秘巨手等意象,合构成一幅充满想象力的具有奇幻神圣色彩的画面,其既有对人间社会、自然万象的概括刻画,又有对信仰世界的含蓄表达,内涵复杂而丰富。从玉璋刻绘图像分析,大体可以推测该图像应是隆重祭祀场面的写照。但玉璋的图案还有许多未解之谜,比如下层跪着的人和上层站着的人是什么关系,是否表示人间与神界?人物不同的姿态是否表意祭祀的仪式流程?图像中悬空的不规则几何图形又是表现什么?可以说,三星堆文物的神秘性在这件玉璋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共出土玉璋57件,大致分为三类:一类为边璋,斜边平口,略呈平行四边形;一类为牙璋,呈长条状,该类器物在陕西神木石峁龙山文化、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但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牙璋数量最多,制作最为精美;一类为鱼形璋,璋的“射”部酷似鱼的身体,“射”端呈叉口刃状,宛如微张的鱼嘴。鱼形璋是蜀地特有的器型,目前仅见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
三星堆典型的玉石文物还有玉璧、玉琮、玉斤、玉刀等,两个祭祀坑出土的众多玉石器足以证明,至迟在商代,古蜀人已有了较为完备的宗教礼仪制度,反映出古蜀国已具有相当强盛的综合国力,而与之相适应的宗教礼仪制度已臻于完善。《周礼》记载的“六器”是玉璧、玉琮、玉圭、玉琥、玉璋、玉璜,古代祭祀天地四方,即以璧礼天、以琮礼地、以圭礼东方、以琥礼西方、以璋礼南方、以璜礼北方。古人以玉作“六器”,玉之用,天地四方,无所不包。玉器作为通天、通神之礼器,在古人心目之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器中礼器的数量最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蜀国的政治宗教文化。其中如璧、璋等都是古代祭仪中最为重要的礼器,璧以礼天、璋以祭山,“天山之祭”是古蜀人通灵、通神、通天的宗教祭祀礼仪主要方式。
摘自 《中国建设报》 2025.07.10 记者 胡春明 常越